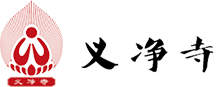

义净专栏
返回 >义净,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出生在齐州山茌县(今济南市长清区张夏镇)周围的一座山庄。
义净的父亲和母亲都笃信佛法,平日以耕读度日,广作善事,闻名遐迩。
祖上曾当过东齐的郡守,后来看到兵荒马乱,豺狼当道,就隐居不仕。到了祖父和父亲这两代,都恪守祖训,在州城旁的一处偏僻山村隐居。几间茅屋,几块薄田,依山傍水,绿荫环抱。农活忙时,每天与农夫为伴,乡亲邻里相处得很好,互相帮助,不分你我。平时教子读书,诵经礼佛,日子倒也过得快乐。
这一年,天气出奇地暖和,七个月内滴雨全无,河流枯竭。禾苗一天天枯萎,造成了多年少见的灾荒,整个河南道和河北道几乎颗粒无收,齐州灾情尤为严重,受灾的人口太多,官府赈济有限。而一些富有余粮的大户却利欲熏心,囤积居奇。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人们快要绝望的时候,忽然传来了一个特大喜讯:城西土窟寺有两位和尚,不但拿出了寺里所有粮食,而且还从泰山神通寺运来了许多。凡是饥民,都可前去就食!人们擎着碗和瓢,诵着佛号,纷纷向土窟寺涌去。
见此情形,义净父亲的愁眉才稍稍舒展。母亲也快步走到佛龛前,拈香祷祝,感谢佛祖保佑,口里不断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义净的父亲想去土窟寺看看,就牵着义净的手向土窟寺走去。土窟寺离义净的家并不太远。绕过河湾,翻过一座小山就是。义净的父亲也常来土窟寺参加佛事活动,所以和土窟寺的和尚们都还熟悉。
父子俩随着人流缓缓走近山门,平常熟悉的了然小师父领他们来到明德法师处。明德法师平日就很喜欢义净,一看到他来了显得非常高兴。父子俩向明德法师问讯后,才发现旁边还坐着两位法师,连忙合十行礼。
明德法师介绍道:“这两位是从神通寺来的善遇法师和慧智禅师,专门放粮赈灾来的。”一面又指着义净父子介绍:“这是山那边张施主父子,一向亲近佛门,乐善好施。特别是这位小施主,天性聪敏,颇有慧根,将来的成就,当不在我等之下。”
善遇法师和慧智禅师一边答着礼,一边注意起了义净。只见这个孩子顶梳双髻,脚穿粉底布履,长得虎头虎脑;又见他刚才跟父亲进门时,亦步亦趋,举止有方,也不由得心中喜欢。善遇法师就笑着问道:“小施主,几岁了?”
义净举起小手答道:“五岁。”
善遇法师又问:“学过经文吗?”
义净答道:“学过,爹爹去年就教我背《金刚经》了。”
善遇法师眼中一亮,把义净拉到身边,不住地称赞。随后,众人谈起了赈灾的事情。义净又默默地站回父亲身后,打量着善遇和慧智两位师父。
善遇法师约五十
...两盏素油灯照亮了佛堂。灯影摇曳,人影模糊。随着钟磬和木鱼的交替敲击,土窟寺众僧在大殿里各就各位,肃然而立,清雅悠扬的诵经声响了起来。
功课作毕之后,义净又拿起新近正在看的《佛国记》。《佛国记》是法显大师对自己求法经过的追忆和记录,均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写得质朴而明畅,很好懂。义净读得十分仔细,时而热血沸腾,时而捶足叹息。
不几天,义净就读完了《佛国记》。他高兴地去找师父,说:“师父,弟子已将《佛国记》读完了!”
慧智禅师笑了笑,但没有说话。
“也许师父是要我多读几遍。”义净琢磨道。于是又认真地读了一遍。
几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义净把《佛国记》不知读了多少遍,乾归国、耨檀国、敦煌、鄯善国、焉夷国……义净几乎能将法显的三十国游历讲一遍!这一天,义净才顿时省悟道:“师父不是说过要有大志向!我把书读了这么多遍,可我的志向是什么呢?”义净百思不得其解,决定找个机会就这个问题请教慧力师兄。
土窟寺有十几亩地,大部分种粮食,离寺最近的一块地种菜。一天,众僧正在寺田的菜地锄草。休息的时候,义净问慧力师兄:“师兄,你的志向是什么?”慧力感到莫名其妙,停下手中干着的活,边擦头上的汗边问:“师弟,什么志向?”
“就是师兄自己的志向。”义净重复道。
“我的志向?”慧力略思索了一下,突然拍拍手道:“对了,身入佛门不就是我的志向么!”
对!身入佛门不就是志向么!弘扬佛法,救济群生不就是“大志向”么?义净高兴极了,等锄完菜回到寺里,马上去找师父。
“师父,我有志向,我的志向就是弘扬佛法,救济群生!”义净高兴万分地告诉师父。慧智禅师听了,微微笑了一下,却反问道:“净儿,你已经快十七岁了,你怎样来弘扬佛法?用什么来救济群生?”
义净愣住了,不知怎样回答才好。此后很长时间,义净一直在苦苦思考:怎样来弘扬佛法?用什么来救济群生?他想了许多答案,但都觉得不满意。师父所说的“大志向”究竟是什么呢?没有办法,义净只得去问师父。师徒两人向来亲密无间,义净对师父是无话不谈的。义净把自己的想法和问题禀告了师父。师父温和地问:“净儿,有次你早晨上堂去晚了,还系错了一根纽带,记得吗?”
“弟子记得。”义净答道。
“究竟为什么去晚了?”师父又问。
“那天晚上和师父说话,听师父讲法显大师。回去后徒儿睡不着,后来睡着又做起梦来,梦见自己也像法显大师一样,去西方佛国求法。梦中快要到佛国的时候,忽然云板敲响了。”义净老老实实地向师父道。
“想去西天佛国
...唐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艳阳高照,云淡风清。义净手持锡杖,身背装满经籍和随身资具的板笈,在通向长安的官道上踽踽而行。十天后到达洛阳。
洛阳是新设的东都,与长安并称为东西两京,不仅是仅次于长安的全国政治中心,而且佛教事业历来都很发达。义净走近城东的上东门时,发现有许多军兵把守,盘查得非常严。他停住脚步,掏胸前装的身份证明——黄绢度牒。这时,身旁一位青年僧人主动和他谈论。义净一听,问道:“听口音,师兄是山东人?”
“是的,我是莱州人氏,在大觉山大觉寺。”那位僧人说着,从后面帮义净扶起板笈。
原来这位青年僧人法名叫弘祎,是莱州(今山东省掖县)大觉寺的僧人,比义净小两岁,戒龄也短两年。弘祎这次西来也是游方参学,想去长安。不过他来洛阳已经半年多了,正在洛阳听习弥陀净土法门。特别使义净高兴的是,这位弘祎的本业是专攻毗昙,是位论师。义净这次离开齐州来长安的目的之一,就是学习《俱舍论》、《唯识论》等论藏典籍。
都是山东的青年学僧,都是出外求学,骤然相遇,两人立刻便成了好朋友,以师兄、师弟相称。弘祎来洛阳时,经大觉寺师父的推荐,住在净土寺。该寺在毓财坊,进上东门,向左走过积德坊便是。义净刚到洛阳,还没决定去何处挂单,应弘祎的热情邀请,便高兴应允来到净土寺。
弘袆论师早来半年,对洛阳的情况已很熟悉。他虽也是客僧,但对义净来说却成了主人。弘祎热心地向义净介绍各处名胜,并自告奋勇领义净去几处重要的地方朝拜。
一晃,就到年底了。这天,一阵猛烈的西北风过后,下起了雪。雪越下越大,纷纷扬扬,弥天漫地,马上路上便积了厚厚一层。义净和弘祎不能外出参学,便呆在屋里阅经。突然,弘祎论师说:“义净师兄,我想再过几天咱们出发去长安,你觉得如何?”
长安铁定是要去,但义净还没决定何时动身。听弘祎说过几天就走,便有些奇怪。“为什么过几天就走?”义净问。
“师兄还没有观礼过迎请真身舍利的盛况吧,真身舍利如今就在大内供奉着。愚弟听说将要送往长安供养,然后再由长安送入法门寺真身舍利宝塔中。咱们赶往长安,可以观礼奉送的盛况。”弘祎答道。
义净在齐州的时候就听说了佛祖真身舍利的事情,但是不知道舍利究竟是什么样。现在听弘祎说赶往长安可以观礼奉送的盛况,不由得动了心。洛阳虽然也是京城,佛教事业兴旺发达,但比长安还差一些。
两天后的早晨,大雪终于停了,阴云缓缓散去,露出了一轮红日。义净和弘祎辞别了净土寺,双双背着板笈上路。后来在中途又增加
...唐高宗麟德元年(664)二月五日,晚上四更刚过,关中北部坊州的南城门忽然吱呀呀开启,穿出一区骏马。未等城门在闭,骑者与骏马早已飞驰而去!
月色朦胧,群山静寂。只听得阵阵急促的马蹄声在山间石道上脆响。马蹄声由北向南,穿宜君,绕同官(今陕西省铜川市),下华原(今陕西耀县),直奔长安。三个时辰后,飞骑已至长安开远门。交验腰牌和文书后,又马上朝东奔向皇城。
骏马的铁掌敲响了长安城大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随之,另一个消息更使得长安僧俗吃惊不已:朝堂上响起一片哀恸之声,皇帝罢朝三日,一个噩耗迅速传遍了长安,传向全国各地:大唐三藏法师玄奘于二月五日夜半在坊州玉华寺逝世。
大慈寺突然响起了急促的钟声,正要出门的义净和弘祎、玄瞻又回到了大殿前。僧众齐集后,上座法师双手合十,未说话已泪流满面:“我玄奘大师昨日晚已谢世往生。众僧随老衲到佛祖前诵经,祈请佛力加被,大师早登兜率天境。”
好似当头一棒,如同万丈高山一脚踏空,义净只觉得—阵眩晕,腿脚发软。千里迢迢来到长安,大师却去坊州译经。原想等大师回京后即去拜谒,向大师诉说自己的心愿,请大师指点迷津,去除疑惑,却不料如此无缘,自己如此福浅命薄。
寒风呼啸,天地昏暗,整个长安城沉浸在悲哀之中。朝廷下令,玄奘大师葬事所须费用,全部由国家供给。
4月14日,玄奘大师将被安葬在长安城外的丈河旁。送葬这天,长安僧尼和士庶送来了素盖、幡幢、帐舆、金棺、银参、娑罗树等,达五百余座,分布在城内大街要道上。方圆五百里以内,四面八方的人流,都涌向长安城东丈河旁的白鹿原,人数达一百余万。当时长安城内的总人口仅约百万,这次送葬,好比是万人空城。这在长安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
此情此景,已经使义净热泪满眶:人生能得到这种际遇,更欲何求?只要能济度苍生脱离诸苦,就是死上—千次、一万次也值得!晚上,义净和数万人一样,不顾官府的劝告,守在墓所。也就是在此时,义净心中终于形成了酝酿已久的一个决定,待大师安葬后,马上赶回齐州,禀告师尊慧智禅师,他将继承玄奘大师的事业,赴西方佛国求取圣法,济度苍生。
义净对弘祎、玄瞻、处一说了自己的计划,众人都称赞不已,表示愿意一同前往,共赴险途。
三个月后,义净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将《俱舍》、《唯识》、《摄论》、《成实》等论典都已系统地学完,对各代律学大德的著作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当世律学泰斗道宣大师的著作,也进行了仔细的学习,有许多还是亲耳聆听道宣大师讲述。
暑期
...炎夏,骄阳似火。
扬州的天气像火炉一样,蒸气逼人,没有风,没有云,人们热得就要喘不过气来了。义净和善行在扬州谢司空寺坐夏,今天是最后一天。
日已近午,两人在房内跌坐。离开齐州时的高兴和激动已荡然无存。义净闭目不语,善行一脸沮丧的样子,常偷眼看看师父。义净虽说闭目不语,可内心如风起云涌,极不平静。头上的汗一道一道淌下来,却擦也不擦,仍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当初在长安结志西游的处一法师,因侍奉母亲而不能去了;现在弘袆和玄瞻也改变了初衷,要专修净土法门,也不愿去印度了。
怎么办?
善行明白师父的心情,有心安慰,但不知说什么才好。不禁瞥了瞥师父身旁的一个包袱,那里面是一匹琵绢和一件如来等量袈裟。听说义净要赴西天佛国,齐州诸寺和百姓送来很多织绢,乞求义净带往印度供施。义净望着那堆成小山般的织绢发了愁。中土与印度远隔千山万水,怎样才能将它们带去?后来,慧智禅师想了一个办法,将送来的这些织绢每匹剪下一块,最后缝合到一起,剩余的都退还。用缝合到一起的这些绢,裁制了一件如来等量袈裟,恰好还剩有一匹。虽说只有一匹琵绢和一件袈裟,可这是山东道俗对佛祖的一片心意啊!情义之重,不亚于一座泰山。
义净下定了决心:初衷不改!
可是水路和旱路不同,得准备许多的淡水和食物,尤其是搭便船的问题。
这时,谢司空寺的上座法然大师和维那观性律师进来了,还有一位沙弥提着一个食盒。另一位是俗人,义净不认识,义净忙放下琵绢、袈裟,站起来敬礼。
“听善行小师言,律师身有微恙,没有去用斋,老僧与施主专门前来看望。”法然大师又转身接着向义净介绍道:“这位是龚州刺史冯大人,发愿来敝寺普斋僧众。全寺上下都已用过斋饭,单单缺你们二人,冯大人执意来送果品和点心,以求功德圆满。”
天气这么炎热,冯刺史竟亲自来送斋供。义净忙给各位让座。众人落座后,冯刺史看见床榻上的琵绢和袈裟,问道:“此绢和袈裟为何都是碎片缝成,又似乎都是新的?”
“这是齐州佛门弟子献给佛祖的供奉之物,因人数太多,只好从每匹织绢上剪下一块,缝合而成。”义净回答。
“南无阿弥陀佛!”刺史又问道:“佛祖远在天竺,不知怎样送去?”
“贫僧发心赴天竺求法。”义净就将自己的计划及目前的问题简单讲了一遍。
“如此甚好!”刺史赞同地点了点头,高兴地说:“只要大师有此勇心,旅途之事不用担心,一切由下官承办。再者,下官两位舍弟俱在原籍冈州(今广东新会市)州府任职。冈州与广州都是出海口,南海诸国商舶以至波斯商舶
...六个月之后,义净的梵语水准已有了一定的基础,能进行有关日常生活的简单对话了,便收拾行装,再次搭船西行。
这次乘的是室利佛逝国去印度的官船。官船共两艘,目的地是东印度。听说有大唐高僧赴印度求法,国王派使者给义净送来很多供养。所以一切都还顺利,只是风力较小,船行得慢些。十五天后,到达了末罗瑜国。该国在苏门答腊岛的西北部,也就是马六甲海峡的西口。船在末罗瑜停留了两个月,装卸货物。后来又升帆起航,航向西北。十五天后,到达羯荼,即马来半岛的西部。
羯荼是个不大的海港,向西隔着大洋,与印度半岛相望。据船主说,此行直向西北,到东印度的耽摩立底国,顺利的话,二十多天就可到达。行程远,走的又是大洋中部,所以两艘船舶在羯荼作了最后一次检修,备足了淡水和食物,便一前一后,升起长帆。驶出了港湾。慢慢地,陆地不见了,海水和天空融合为一种颜色,无边无际。
义净每天在船上定时诵经打座,然后或许研习律义,或许复习梵语。下午,特别是傍晚时分,便登上舱面,在甲板上散步。晚霞映在海面上,是那么的绚丽多彩。向着落日的方向望去,如同一匹匹巨大的绸缎铺在海面,五颜六色,随着波浪在缓缓地起伏、飘动,恰似一条通向太阳的丝绸之路。每当这个时候,义净总是激动不已:在这条丝绸之路的那边、太阳落下去的地方,不就是西天佛国么!从发愿西行至今已经二十年了,多少次梦中的景象就要变为现实了,就要踏上佛国净土了,就要像法显大师和玄奘大师那样去巡礼圣迹了,就要将山东父老托自己带的那重逾泰山的琵绢和袈裟献给西方佛祖了!
南无阿弥陀佛!佛祖保佑最后这一段航程平安吧。
这一天拂晓,突然遇到一只小船,那位船主说前面是“裸人国”,土人不让通过,他们船上已有一位军士中了毒箭不治而亡。他们等在这里,盼望两船联合,集中武器冲过去。
但这边的船主却摇摇头,不主张用武力解决问题。这位船主年纪要大得多。船主的航海生涯已经很长了,这可以从他黝黑的脸膛和满脸深深刻着的皱纹中看出来。老船主不慌不忙,微笑着向水手们示意:起碇升帆!
老船长向舵手指示了方向后,带了两个水手下到内舱,来到义净住处的旁边。义净已经注意到门口有一木板箱,很重。船主命令水手打开箱子,里面全是铁器,有铁刀、铁矛头、铁钉、铁弓等等,只不过很旧了,大多数锈迹斑斑。船主命水手将箱子搬了上去。
“阿弥陀佛!全都是武器。菩萨慈悲,希望不要打起来。”义净瞥了一眼,心中暗暗祈祷。
“呜——”传来一声螺号声。义净忙爬上舱面察
...学完了《声明论》,义净心情舒畅,便与大乘灯禅师商量去中天竺巡礼之事。
大乘灯禅师说:“咱们如今虽在天竺,可是巡礼圣迹的事,并不是那么容易,须好好筹划方可。”
“为何已在天竺,巡礼圣迹还不容易?”义净有些不明白。
“印度不比我大唐,”大乘灯禅师道:“说起地域,印度比我大唐稍小,可政治的治理远比我大唐复杂。我大唐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可印度却有十几个国家,各不相属。还有不少部落,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而且崇信邪神。因此之故,路途的风险并不比从广州到这里小!”
西天佛国竟是如此的现状,这大大出乎义净料想之外。只听大乘灯师又继续说道:“从这里去中天竺大觉寺,有两千里之遥。我听说沿途山高林密,常有强人出没,劫财害命。要是前去,须得结伴而行方可。几百人、上千人一起去,方可保无虞。”
义净心里疑虑重重。一了解,果然如大乘灯禅师所说,去中天竺须结伴而行,而且已约定俗成,每半月走一次。所有去中天竺的人,每半月的某天,在城西大路口会合,日中以前出发。沿途有许多地旷人稀的地方,食物难办,需多带干粮。况且,雨衣雨具也是必须的。如此一来,连行装资具和经籍,以及义净从齐州带来的琵绢等,东西不少,份量也不轻,两人怎么背得动?何况大乘灯禅师已五十余岁,虽然雄心勃勃,可毕竟体力已衰。
大乘灯禅师久居此地,情况较熟,便出去联系了几次。碰巧有一批那烂陀寺的僧人,前来运化募的食油回去,得知有唐地僧人想去大觉寺,便慨然应允,将两人的行装装载在运油的车上。准备妥当后,义净与大乘灯禅师按时来到城西大路口,跟着人群一起,开始了两千里的行程。
西行的人群大约有五六百人。从皮肤颜色看,有黑种人、黄种人和白人,从身份看,有僧侣、旅行者、探亲者,甚至还有官府的差人。多数是男人,妇女和儿童很少。有的乘车,有的步行,还有的骑马。人们互不相识,只是由于共同的利害关系走在一起,因此五花八门,五颜六色,使义净觉得很有趣。
两天后,便进入了山区。山不高,但树木十分茂盛。五六百人走在一起,吆喝之声,此伏彼起。夜晚,生起十几个火堆,人们席地而坐。火焰熊熊,不仅壮观,而且也很热闹,使人们忘却了旅途的危险和疲劳。然而,这种好事却持续得不长。从第三天下午开始,浓云密布,下起了暴雨。到了第四天,山洪暴发,到处都成了泽国。五六百人在水乡泽国困难地跋涉,苦不堪言。
祸不单行,偏偏在这个时候,义净患了疾病。病初起时,感到寒冷异常,浑身水淋淋的,颤抖不止。随后又遍体发热,汗如
...义净与大乘灯禅师在寺内观瞻,每遇尊像圣迹,必然毕恭毕敬地合十参拜。他们刚拜完一座大塔,准备离开,一回头,却和一位僧人碰了个照面。义净正要合十问讯,不想那位僧人却问道:“两位法师可是从东土大唐来?”说的竟是唐语,而且还是地道的长安官话!
“正是!”义净惊喜交加,忙问道:“法师好像也是从唐地来?”
“贫僧法名玄照,这已经是第二次来那烂陀寺了。两位初到,有不便处可找贫僧。贫僧是奉大唐朝廷圣旨前来的。”玄照法师很热情地说道。
他乡遇故人,义净与大乘灯禅师当然是欣喜万分。
玄照法师是京城东边的太州仙掌(今陕西省华阴县)人,俗家本为世族。幼年出家离俗,成人之后便发誓游历西方,观礼佛迹,因此,在京城大兴善寺学习梵语。学成之后,便杖锡西迈,经过西域流沙南下。当时唐、蕃交好,文成公主刚到吐蕃不久。玄照到了吐蕃,蒙文成公主多方照顾,派人将他送到了北印度。此后,他便独自巡礼圣迹,学习经论,达十年之久。
显庆四年(公元657年),朝廷派使臣王玄策出使印度。王玄策回国后,上书玄照法师在印度德行俱佳,有口皆碑,因此朝廷颁发诏书,追玄照回国。玄照回国时,高宗皇帝在东都洛阳,听说迦湿弥罗有位一百岁的婆罗门,名卢迦溢多,藏有仙方,善制延年益寿之药,高宗便让玄照赴迦湿弥罗迎请卢迦溢多。玄照法师又一次来到北印度,见到卢迦溢多后,卢迦溢多答应入唐,但说药物不够,就先随另一路使者入唐,让玄照法师另带两人到西印度、南印度包取药物,之后返唐复命。
玄照法师带了两位从人,费尽辛苦找到了药,却发现有国归不得。原来唐蕃关系恶化,吐蕃道路不通,而西北印度却又有大食入侵。无奈之下,就逗留在那烂陀寺。同他一起来的两位随从也是出家人,看到归国无望,也都漫游于印度各寺,一位法名叫师鞭,另一位法名叫慧轮。
义净与大乘灯禅师知道了玄照法师的传奇经历后,蹉叹不已。人生的机缘,真是无法预料!玄照法师有国归不得,圣命难复,突然遇见两位故国来的人,心情马上舒畅了不少。
观礼了那烂陀寺以后,义净和大乘灯禅师在玄照法师带领下,去观礼灵鹫山。这座山也在王舍城以北,但是位置稍微偏东,距离那烂陀寺只有十几里路。过去佛陀住世时,常居此山演说妙法。三个人拿着香烛,边走边说着话。一个时辰后,灵鹫山到了。放眼望去,山并不是很高,但巍然独立,满山葱茏。几只硕大的鹫鸟,在天空盘旋,悠然自得。三人议论着当年这里的盛况,感叹他们生当末法时代,无缘亲聆圣教。
来到山顶,地势稍平坦,东
...那烂陀寺的生活简单而有序。义净在这里的学习比较广泛,大致分两类:一类是当时流行的中观、瑜伽学说,稍偏重于瑜伽,另外还有因明、俱舍等;另一类就是戒律之学。这后一类是义净的专业,也是义净来印度求学的目的。对此,义净不仅认真地学,还大量地抄写。为了将所学传回东土,义净经常练习翻译,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一百五十赞佛颂》等典籍,就是在那烂陀寺译成初稿的。
时光易逝,十年过去了。
在这十年中,由北路通往大唐的道路依旧被阻塞,玄照法师溘然而逝,运送药材返唐复命,竟成了泡影。待义净如亲人一般的大乘灯禅师,也于拘尸城佛涅槃处圆寂。临终时他托人捎话给义净,一定要将大法传回东土!听到玄照法师逝世的消息,想起一同在必摩罗跋城的情景,义净沧然涕下,挥笔写下了一首情真意切的诗歌,表达了自己的倾慕与哀悼之情。
这一天,义净同另一位从唐地来的僧人无行禅师登上灵鹫山。站在山顶上,想起故友相继去世,遥望远方,故国渺然。慧智师父他们也不知怎么样了?……百般滋味涌上了心头,又加上思乡情切,他忍不住写了一首一三五七九言的宝塔诗:
游,愁!
赤县远,丹思抽。
鹫岭寒风驰,龙河激水流。
既喜朝闻日复日,不觉颓年秋更秋。
已毕耆山本愿诚难遇,终望持经振锡往神州!
龙河就是尼连禅河,在佛陀成道处附近。耆山,即灵鹫山。赤县、神州,都是指东土大唐。虽然义净西游,遇到了许多不如意的事,但将大法传回东土的心愿,却始终不曾动摇。这是义净冒死求法的目的。眼见得来印度的唐地僧人一个个离世,大愿未了,更增强了义净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义净完成了学业,抄好了经律,在打算回国的时候,依旧没有忘记那些客死异乡的求法僧们。这些人中,义净认识的有大乘灯、玄照、佛陀达摩,对那些不认识的,义净也多方打听他们的籍贯和求法事迹。他们是齐州道希、师鞭,并州道生、常悯,长安末底僧诃、玄会,益州智岸,交州木叉提婆、窥冲,布州智行,荆州法振、乘悟,洛阳昙闰、光辉等等。另外,不知下落的求法僧,还有益州明远、义朗、义玄、会宁,交州慧琰,荆州道琳、昙光,洛阳智弘。那时还健在的仅有并州道方、荆州无行以及和玄照、师鞭同奉诏到印度取药的慧轮。他们有的是死在赴印度的途中,有的死在印度,也有的死在回国的途中。这真是:高僧求法赴西土,去人成百归五十!
临回国前,义净又专门去了趟大觉寺,求了一尊真容圣像和三百粒舍利。从大唐带来的琵绢和袈裟就披奉在这样的圣像上,他要回去向故乡的道俗复命。做
...洛阳城里的老百姓们,听说有大法师来到洛阳,连皇帝都准备亲自出迎,城门边早已是人山人海。人人擎着香柱,个个口颂佛号,争先恐后,都想一睹大师的风仪。从上东门外开始,数十里之内,已经布满无数军兵,维持秩序。洛阳成百座佛寺,都搭制卜车、帐盖,僧众们手持香花,唱着赞呗,整齐地站立两边,正中是朝廷百官相迎,数百面旗幡迎风飘扬!
义净一行来到了上东门前,忽然一切都安静下来,只见正中门下,百官闪向两边,现出了当今的大周女皇。她头戴旒冕,身披黄袍,雍容华贵,含笑而立。内侍扶义净下了御车。义净定了定神,从容地走向武则天面前,合十致意。则天见状,也口称弟子,躬身施礼。而后,众内侍又扶义净上了御车,当先入了上东门。这时,又旗幡招展,乐声大起。洛阳城内也随处是卜车、牌坊,所过之处,香烟如云,颂佛号声不断!
车流、人流停在了建春门内的佛授记寺,义净及其带回的舍利、佛经、佛像,都被放置在这所皇家寺院内。随后,敕旨下达:封义净大师“三藏”之号,可马上着手翻译带回的经论,由朝廷提供一切便利。当时有“三藏”之号的僧人全国仅仅有四位,其他三位都是外国的高僧,只有义净是本国人。
就在义净准备翻译带回来的佛经时,这年十月,内侍又奉宣圣旨,请义净三藏移住大福先寺,参加编写大周的《众经目录》,并和于阗高僧实叉难陀等共译《华严经》。这两项工程进行了四年才算完成。
大周久视元年(700)五月五日,东京洛阳大福先寺翻经院内,正在举行一项庄严神圣的仪典。身为大周帝国国立译经场的译主,义净三藏端坐在翻经院大堂的正中,译经场的其他成员,在两侧雁翅般排列。除了一位朝廷官员外,其它都是僧人。
义净面前放着一部新译的经书,叫《入定不定印经》。只见他在经书上浏览了一下,然后双手合十,抬起头来,向座下两侧扫视了一遍,高声说道:“各位大德法师!上托佛祖佑护,下有国主相助,仰赖各位不懈努力,《入定不定印经》今天已经圆满译成。南无释迦如来!”
众人在下面也合十应道:“南无释迦如来!”
义净又接着说:“如今,新译《入定不定印经》将进上朝廷,请国主御览后,批准在天下流通。义净恭请各位三思:对所译《入定不定印经》的音义,是不是尚有怀疑的地方?万一有,就请各位明言!”
众人没异义,全都在上面签名。译主义净亲自写好表章,连同新经一起,由监护奉呈给朝廷。则天皇帝观看了表章和新经,凤颜大悦,亲自为新经写了一篇《三藏圣教序》。
义净严守清规,淡泊宁静,一门心思扑在了译经工
...